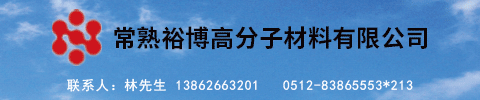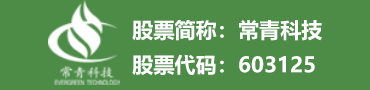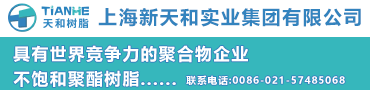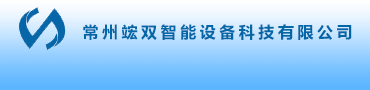上海石化与复旦大学协同创新开发高性能碳纤维
“要1300年!假设每个工艺过程中只调节两个参数,每个参数实验3个点,每天做10个实验,就要试上1300年才能完成。”
“忙了40多年!国内企业研发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起步,但进展缓慢,虽有零星生产,可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无法跨越产业化的门槛。”
这里说的就是碳纤维,也被称为“黑黄金”。
它是未来材料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却一直是国内企业和研究单位解不开的心结,耗时多年,徘徊不前,焦虑与无奈并存,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
可谁都不曾料到,从2008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以杨玉良院士为的高分子科研小组的支持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短短四年,就完成了碳纤维全新的工艺研发,次打通了从原丝到碳丝生产的全流程。如今,一条年产3000吨原丝、1500吨碳纤维的生产装置正在紧张建设。
“高校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企业的工程化技术开发无缝对接,让我们不用‘摸黑前行’,不用无谓地模仿与试错,‘在知其所以然’的前提下少走了许多弯路,跨越了鸿沟。”上海石化副总经理张建平表示,到明年年底工程全部投产后,就可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地位。
“21世纪是碳纤维世纪”
在上海石化腈纶部的展示室内,我们目睹了“黑黄金”的真面目。看似普通的一卷卷的黑丝,却不同凡响。它的密度和质量仅为钢的1/3,可抗拉伸强度是钢的4至9倍。
新的波音787飞机,高性能碳纤维占其体重的20%,可省油30%以上;用碳纤维替代玻璃钢的海上风力发电设备,叶片直径可达100米,发电效率大幅提升,还能经受海水腐蚀;一辆用碳纤维制造的山地自行车,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提起来,可更坚实、牢固……
“有人说,19世纪是钢的世纪,20世纪是塑料的世纪,21世纪是碳纤维的世纪。”上海石化腈纶部总工程师黄翔宇告诉记者,如今,碳纤维开始在各个新型领域得到实验和应用,其中58%用于一般工业,23%用于休闲体育,还有19%则用于航空航天以及军事装备领域。然而,多年来,仅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拥有并掌握碳纤维生产技术,日本的东丽、东邦、三菱人造丝等三大公司,产量占的七成。他们从来不在海外设立原丝厂,牢牢掌控碳纤维关键技术,“不漏半点风声”。
过去,国内自主研发“举步维艰”。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步骤繁多,程序极其复杂,其间伴随的化学变化包括脱氢、环化、预氧化、氧化及脱氧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细微变化,就可能让整个研发陷入 “死胡同”。40多年来,不少国内企业前赴后继,一次次试验,可没有人真正走出迷宫,实现产业化。业内直呼,“碳纤维这水有点浑、有点深!”
那么,上海石化携手复旦大学,又是凭借什么“独门绝技”,短短4年找到打开碳纤维大门“钥匙”的呢?
架起理论和工艺的桥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杨玉良一语破题:碳纤维的生产路线很长,主要分为聚合、纺丝、牵伸、预氧化、环化和碳化等工艺流程。如果按照传统“炒菜式尝咸淡”的试错模式,再过上千年也找不到碳纤维的“真谛”!
成为“黑马”,关键在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思路:利用基础理论研究,从“根上”解决了碳纤维研制的原理。杨玉良说,碳纤维的研究基础的仍是高分子科学,这是复旦大学绝对的强项,碳纤维无论如何变,“万变不离其宗”。
而对上海石化来说,“牵手”复旦大学,初有点“小意外”。黄翔宇说,在以往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更愿意与离产业化更近的工科院校合作,与复旦这样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高校少有 “交集”。起初,在市经信委等部门的牵线和支持下,双方走到一起。可面对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复杂理论模型,上海石化的工程师们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连串一连串的公式,看得头都大了。”上海石化腈纶部副总工顾文兰虽然是科班出身,也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套路:这“花架子”有用吗?复杂数字运算和理论模型,能与一根根精品碳化细丝联系起来吗?
次打消疑虑,让双方互信,始于纺丝流程中的“喷丝难题”。
顾文兰说,在中试时的纺丝阶段,次喷丝时,1.2万个细小喷头中竟有30%左右没有出丝,即3600个喷丝孔“放空”,这离12K束的标准还差很远。上海石化从以往生产腈纶工艺经验认为,是喷丝头的粗细等机械结构出了问题。于是,不断换喷头,从A系列一直换到K系列,依然如旧。“当时都有点傻了,每天守着喷丝头,希望奇迹能够发生。”那段时间,顾文兰茶不思,饭不想。
而此时,在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复旦课题组成员则通过物理高分子理论、数学计算、计算机模拟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喷丝头上,而在内部温度控制上。教授们将几十页的数字、公式化成简单的文字,递给上海石化,大家一下子茅塞顿开。根据复旦提供的参数重新设计设备,上海石化仅仅一个月就将设备零件超要求设计出来,如今出丝率稳定在96%以上。
“有了方向,路再远也不怕”,顾文兰说,以前总是没方向,按照经验不断试,现在才体会到 “理论的力量”。
于是,信任的力量化成一座桥梁,让一个个“金点子”,在复旦基础理论研究与石化工程工艺设计之间“不断跳跃”:
在纺丝凝固阶段,由于原丝内孔洞过多,导致强度变低。复旦课题组从“膜科学”要求孔洞多而均匀的原理,反其道而行之,化解了原丝致密性问题。
在原丝碳化阶段,理论数据直接用在工艺设备上,出现断丝率偏高现象,而上海石化通过以往经验调试,修正了理论与现实存在的偏差。
“1+1>2”关键在“无缝对接”
高手“牵手”,并非都是“1+1>2”。近年来,上海石化也与一些高校进行了大量产学研合作,有的也“虎头蛇尾”,留下诸多遗憾。
黄翔宇说,“对与高校的合作,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包括这次与复旦到底能不能做成,起初心里也没底。”在他印象里,高校的教授几乎都是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基本没时间与企业亲密接触,挂个产学研的“帽子”弄点经费,后都是草草结题,谈不上产业化。
可这一次,杨玉良院士带队的课题组,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
虽然一个地处上海西南角,一个地处东北角,“沟通之路”却异常近。每过几天,上海石化的课题组都要带着“一大串问号”,奔向东北角。而复旦的教授们,每个月也要定期“东南飞”,在厂房内现场解决问题。
在采访中,“读懂对方”是双方课题组多次提到的词汇,背后蕴含的就是“无缝对接”。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院士总是亲力亲为,始终把住工艺与理论的大方向。“只要杨校长在学校吃中饭,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他,那就是碳纤维课题组。”张红东教授说,“正是‘从头到尾’都搞得懂、理得顺的杨校长,才让双方的沟通变得简单有效。”黄翔宇说,每次听完杨校长的讲解后总能豁然开朗。有时,当时听懂了,回去面对设备的时候又糊涂了,杨校长则会不厌其烦地再次认真讲解。按照杨校长的讲法,“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往往都是同一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方法而已。循环几次,企业的科研人员真正掌握了理论的精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幅提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旦课题组的团队中,各位教授各有特长,从化学合成到理论计算、从计算机模拟到加工工艺,形成一根长长的链条。比如,在初的聚合反应阶段,由擅长高分子化学的何军坡教授把关;在纺丝阶段,由在高分子物理和计算机模拟领域颇有造诣的张红东坐镇。这样一来,面对碳纤维复杂冗长的流程,各个教授分头把守,又充分合作。每位教授不论身在何处,对上海石化的问题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由于之前协议明确了利益分配,双方都不会互相“留一手”,建立了一种不加提防、全盘托出的信任。
黄翔宇说,慢慢地,我们从工艺的角度读懂科学理论和数字模拟,发现它们也是形成生产力的利器。
杨玉良院士话语中肯:“让企业认识到理论的价值,让高校认识到企业的擅长,这样的团队才能形成合力。”
于是,在双方团队协力下,研发和生产调试快速挺进:2008年11月,建成中试装置;2009年3月,成功研制出12K原丝;2011年12月,千吨级装置阶段部分试运行……
扩大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
合作四年下来,双方的感触不少,大家也思考,这样的“无缝对接”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领域吗?
杨玉良认为,有的产学研项目不成功,是因为“分段承包”、“科研拼盘”,这样做带来的大问题是相互扯皮、自以为是,明明是纺丝有问题,可能会将责任推到聚合环节;明明是牵伸环节出了问题,可能会说是喷丝有问题。在这次合作中,生产流程的每个环节复旦课题组都配备了精兵强将,做好分工,而上海石化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工艺流程,合作就更有成效。
当然,在涉及面广、研发链条长的大项目中,通晓支撑整个流程体系科学问题的席科学家和熟悉项目管理的“总指挥”人选很重要。比如,在这个项目中,杨玉良院士实际上担当了席科学家的角色,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基础研究及关键问题来指导项目,不至于使整个项目迷失方向;而“总指挥”在石化和复旦这边各有一位,除了专业能力,他们还要算得上半个管理专家,能够将两边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地分配与统筹,而这也是实现“无缝对接”的关键。
上海石化张建平则表示,通过这个项目的协同创新,为企业培育了一批自己的研发和生产技术骨干队伍,这一点企业看重。
如今,上海石化课题组的黄翔宇和顾文兰,都已成为杨校长的学生。“他们的入门是复旦的创,至于怎样毕业甚至当时都没想好。”杨玉良说,但这个模式一定要有所突破,因为协同创新的后落脚点是人才培养,不但要培养高校的一流研发人员,更要培养一批懂理论的企业一线人员,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等到合作项目完成后,为企业留下一笔无形财富。
当然,一些机制上的限制和束缚也需要突破。比如,在这个合作中,复旦大学很多参与的教授、博士,由于项目的保密要求,不能发表相应的论文,这可能影响职称评定。课题组有一位成员就因为缺少一篇论文没能评上正教授,有些可惜。为此,复旦近期也在商讨,专门针对类似的重点协同创新项目,制定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措施,把职称名额直接下派到课题组,从而保证产学研合作成果显著的参与人员,即使不发论文,也能评上教授。
“忙了40多年!国内企业研发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起步,但进展缓慢,虽有零星生产,可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无法跨越产业化的门槛。”
这里说的就是碳纤维,也被称为“黑黄金”。
它是未来材料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却一直是国内企业和研究单位解不开的心结,耗时多年,徘徊不前,焦虑与无奈并存,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
可谁都不曾料到,从2008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以杨玉良院士为的高分子科研小组的支持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短短四年,就完成了碳纤维全新的工艺研发,次打通了从原丝到碳丝生产的全流程。如今,一条年产3000吨原丝、1500吨碳纤维的生产装置正在紧张建设。
“高校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企业的工程化技术开发无缝对接,让我们不用‘摸黑前行’,不用无谓地模仿与试错,‘在知其所以然’的前提下少走了许多弯路,跨越了鸿沟。”上海石化副总经理张建平表示,到明年年底工程全部投产后,就可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地位。
“21世纪是碳纤维世纪”
在上海石化腈纶部的展示室内,我们目睹了“黑黄金”的真面目。看似普通的一卷卷的黑丝,却不同凡响。它的密度和质量仅为钢的1/3,可抗拉伸强度是钢的4至9倍。
新的波音787飞机,高性能碳纤维占其体重的20%,可省油30%以上;用碳纤维替代玻璃钢的海上风力发电设备,叶片直径可达100米,发电效率大幅提升,还能经受海水腐蚀;一辆用碳纤维制造的山地自行车,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提起来,可更坚实、牢固……
“有人说,19世纪是钢的世纪,20世纪是塑料的世纪,21世纪是碳纤维的世纪。”上海石化腈纶部总工程师黄翔宇告诉记者,如今,碳纤维开始在各个新型领域得到实验和应用,其中58%用于一般工业,23%用于休闲体育,还有19%则用于航空航天以及军事装备领域。然而,多年来,仅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拥有并掌握碳纤维生产技术,日本的东丽、东邦、三菱人造丝等三大公司,产量占的七成。他们从来不在海外设立原丝厂,牢牢掌控碳纤维关键技术,“不漏半点风声”。
过去,国内自主研发“举步维艰”。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步骤繁多,程序极其复杂,其间伴随的化学变化包括脱氢、环化、预氧化、氧化及脱氧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细微变化,就可能让整个研发陷入 “死胡同”。40多年来,不少国内企业前赴后继,一次次试验,可没有人真正走出迷宫,实现产业化。业内直呼,“碳纤维这水有点浑、有点深!”
那么,上海石化携手复旦大学,又是凭借什么“独门绝技”,短短4年找到打开碳纤维大门“钥匙”的呢?
架起理论和工艺的桥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杨玉良一语破题:碳纤维的生产路线很长,主要分为聚合、纺丝、牵伸、预氧化、环化和碳化等工艺流程。如果按照传统“炒菜式尝咸淡”的试错模式,再过上千年也找不到碳纤维的“真谛”!
成为“黑马”,关键在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思路:利用基础理论研究,从“根上”解决了碳纤维研制的原理。杨玉良说,碳纤维的研究基础的仍是高分子科学,这是复旦大学绝对的强项,碳纤维无论如何变,“万变不离其宗”。
而对上海石化来说,“牵手”复旦大学,初有点“小意外”。黄翔宇说,在以往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更愿意与离产业化更近的工科院校合作,与复旦这样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高校少有 “交集”。起初,在市经信委等部门的牵线和支持下,双方走到一起。可面对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复杂理论模型,上海石化的工程师们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连串一连串的公式,看得头都大了。”上海石化腈纶部副总工顾文兰虽然是科班出身,也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套路:这“花架子”有用吗?复杂数字运算和理论模型,能与一根根精品碳化细丝联系起来吗?
次打消疑虑,让双方互信,始于纺丝流程中的“喷丝难题”。
顾文兰说,在中试时的纺丝阶段,次喷丝时,1.2万个细小喷头中竟有30%左右没有出丝,即3600个喷丝孔“放空”,这离12K束的标准还差很远。上海石化从以往生产腈纶工艺经验认为,是喷丝头的粗细等机械结构出了问题。于是,不断换喷头,从A系列一直换到K系列,依然如旧。“当时都有点傻了,每天守着喷丝头,希望奇迹能够发生。”那段时间,顾文兰茶不思,饭不想。
而此时,在复旦大学的实验室里,复旦课题组成员则通过物理高分子理论、数学计算、计算机模拟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喷丝头上,而在内部温度控制上。教授们将几十页的数字、公式化成简单的文字,递给上海石化,大家一下子茅塞顿开。根据复旦提供的参数重新设计设备,上海石化仅仅一个月就将设备零件超要求设计出来,如今出丝率稳定在96%以上。
“有了方向,路再远也不怕”,顾文兰说,以前总是没方向,按照经验不断试,现在才体会到 “理论的力量”。
于是,信任的力量化成一座桥梁,让一个个“金点子”,在复旦基础理论研究与石化工程工艺设计之间“不断跳跃”:
在纺丝凝固阶段,由于原丝内孔洞过多,导致强度变低。复旦课题组从“膜科学”要求孔洞多而均匀的原理,反其道而行之,化解了原丝致密性问题。
在原丝碳化阶段,理论数据直接用在工艺设备上,出现断丝率偏高现象,而上海石化通过以往经验调试,修正了理论与现实存在的偏差。
“1+1>2”关键在“无缝对接”
高手“牵手”,并非都是“1+1>2”。近年来,上海石化也与一些高校进行了大量产学研合作,有的也“虎头蛇尾”,留下诸多遗憾。
黄翔宇说,“对与高校的合作,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包括这次与复旦到底能不能做成,起初心里也没底。”在他印象里,高校的教授几乎都是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基本没时间与企业亲密接触,挂个产学研的“帽子”弄点经费,后都是草草结题,谈不上产业化。
可这一次,杨玉良院士带队的课题组,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
虽然一个地处上海西南角,一个地处东北角,“沟通之路”却异常近。每过几天,上海石化的课题组都要带着“一大串问号”,奔向东北角。而复旦的教授们,每个月也要定期“东南飞”,在厂房内现场解决问题。
在采访中,“读懂对方”是双方课题组多次提到的词汇,背后蕴含的就是“无缝对接”。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院士总是亲力亲为,始终把住工艺与理论的大方向。“只要杨校长在学校吃中饭,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他,那就是碳纤维课题组。”张红东教授说,“正是‘从头到尾’都搞得懂、理得顺的杨校长,才让双方的沟通变得简单有效。”黄翔宇说,每次听完杨校长的讲解后总能豁然开朗。有时,当时听懂了,回去面对设备的时候又糊涂了,杨校长则会不厌其烦地再次认真讲解。按照杨校长的讲法,“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往往都是同一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方法而已。循环几次,企业的科研人员真正掌握了理论的精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幅提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旦课题组的团队中,各位教授各有特长,从化学合成到理论计算、从计算机模拟到加工工艺,形成一根长长的链条。比如,在初的聚合反应阶段,由擅长高分子化学的何军坡教授把关;在纺丝阶段,由在高分子物理和计算机模拟领域颇有造诣的张红东坐镇。这样一来,面对碳纤维复杂冗长的流程,各个教授分头把守,又充分合作。每位教授不论身在何处,对上海石化的问题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由于之前协议明确了利益分配,双方都不会互相“留一手”,建立了一种不加提防、全盘托出的信任。
黄翔宇说,慢慢地,我们从工艺的角度读懂科学理论和数字模拟,发现它们也是形成生产力的利器。
杨玉良院士话语中肯:“让企业认识到理论的价值,让高校认识到企业的擅长,这样的团队才能形成合力。”
于是,在双方团队协力下,研发和生产调试快速挺进:2008年11月,建成中试装置;2009年3月,成功研制出12K原丝;2011年12月,千吨级装置阶段部分试运行……
扩大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
合作四年下来,双方的感触不少,大家也思考,这样的“无缝对接”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领域吗?
杨玉良认为,有的产学研项目不成功,是因为“分段承包”、“科研拼盘”,这样做带来的大问题是相互扯皮、自以为是,明明是纺丝有问题,可能会将责任推到聚合环节;明明是牵伸环节出了问题,可能会说是喷丝有问题。在这次合作中,生产流程的每个环节复旦课题组都配备了精兵强将,做好分工,而上海石化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工艺流程,合作就更有成效。
当然,在涉及面广、研发链条长的大项目中,通晓支撑整个流程体系科学问题的席科学家和熟悉项目管理的“总指挥”人选很重要。比如,在这个项目中,杨玉良院士实际上担当了席科学家的角色,深厚的学术功底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从基础研究及关键问题来指导项目,不至于使整个项目迷失方向;而“总指挥”在石化和复旦这边各有一位,除了专业能力,他们还要算得上半个管理专家,能够将两边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地分配与统筹,而这也是实现“无缝对接”的关键。
上海石化张建平则表示,通过这个项目的协同创新,为企业培育了一批自己的研发和生产技术骨干队伍,这一点企业看重。
如今,上海石化课题组的黄翔宇和顾文兰,都已成为杨校长的学生。“他们的入门是复旦的创,至于怎样毕业甚至当时都没想好。”杨玉良说,但这个模式一定要有所突破,因为协同创新的后落脚点是人才培养,不但要培养高校的一流研发人员,更要培养一批懂理论的企业一线人员,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等到合作项目完成后,为企业留下一笔无形财富。
当然,一些机制上的限制和束缚也需要突破。比如,在这个合作中,复旦大学很多参与的教授、博士,由于项目的保密要求,不能发表相应的论文,这可能影响职称评定。课题组有一位成员就因为缺少一篇论文没能评上正教授,有些可惜。为此,复旦近期也在商讨,专门针对类似的重点协同创新项目,制定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措施,把职称名额直接下派到课题组,从而保证产学研合作成果显著的参与人员,即使不发论文,也能评上教授。